31
2023.05
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网上爆红,几天内就获得了四百万的阅读量。各路媒体蜂拥而至,文章作者育儿嫂范雨素和她所在的皮村文学小组,由此进入公众视野。除了媒体报道,还有网站、出版社向她发出薪酬不菲的邀约,但文学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改变了她的生活。
和六年前一样,2023年的范雨素依然租住在北京皮村。她还在打工谋生。京郊的深秋里,身材瘦小的她裹着厚实的紫色棉服,夹杂着银丝的短发扎在脑后。行走在皮村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打工者一样平凡。

皮村入口处大门
当工人遇上文学
“如果我是记者的话,听说有农民工在写文学作品,那我肯定也会去报道。”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小海说。
不只是写文章的范雨素,还有写诗的余秀华、泡图书馆的吴桂春、翻译海德格尔的陈直……当工人与文化活动相遇,往往能引起关注和热议。工人与文学,两者之间似乎有种天然的“冲突感”。这种冲突感既是文学小组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原因,也投射出工友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是《我是范雨素》开篇的第一句话。2017年突如其来的热度,无疑为范雨素的生命之书翻开了新的章节,但执笔写作的还是那个北漂的家政女工,不是什么“作家”“文化人”。

范雨素
图源受访者
2017年后,范雨素不再当育儿嫂,转做时间更灵活的家政小时工——为了把更多时间留给文学,但“主要的精力还是花在了工作上,现在也只是满足温饱。”
“不干活就读书写作”,这是文学在范雨素生活中的分量。她说,文学是为了生活,但还得打工,是为了生存。
范雨素不是没有过用文学求生存的机会。2017年,有出版社拿出20万要与她签约,还有网站给出每月四篇稿件每篇1500元稿费的邀约,她都一一拒绝,因为觉得这会成为自己写作的包袱。最后,她与一家出版社达成合作,对方期望她继续写非虚构作品,而她却交出一部奇幻色彩的小说,最终合作告吹。
令人庆幸的是,范雨素的小说并未因此夭折。去年年底,这部名为《久别重逢》的长篇小说终于出版。无独有偶,皮村文学小组在去年也出版了文集《劳动者的星辰》。他们又迎来了外界新一轮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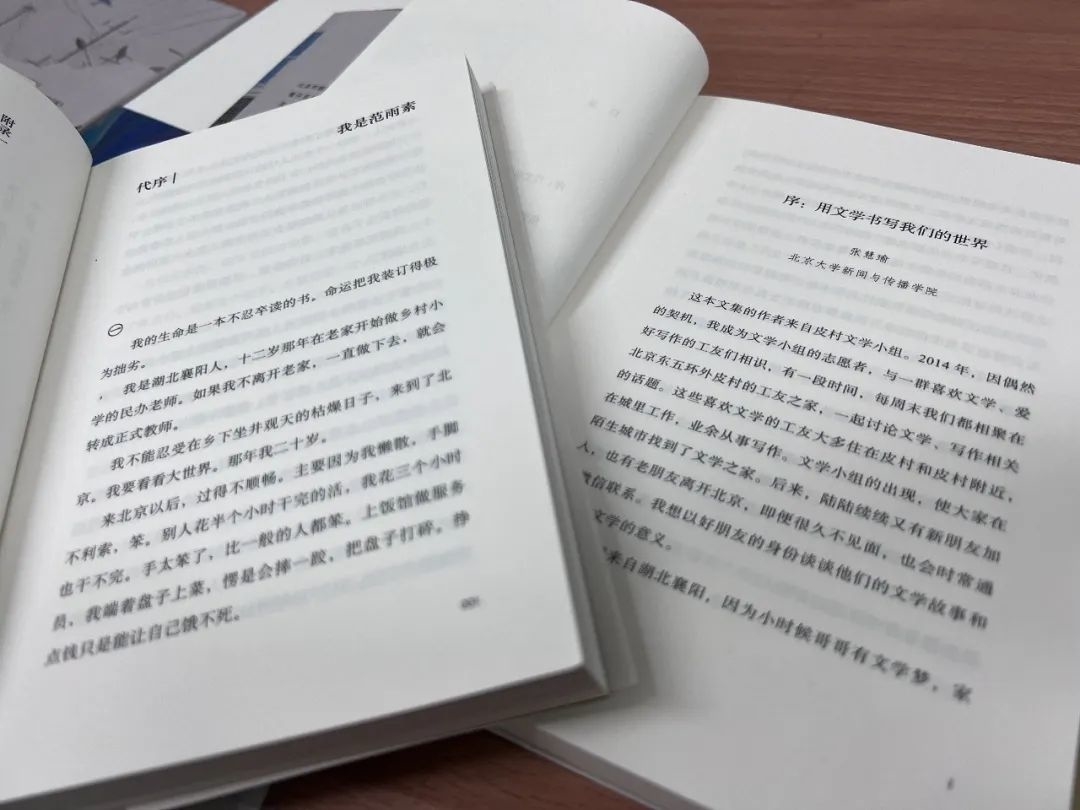
《久别重逢》《劳动者的星辰》内页
和2017年不一样的是,现在的范雨素从容了许多。当年在《我是范雨素》发布一天后,就有10家媒体找上门来。造访者越来越多,她招架不住,只好对外宣称自己躲进了深山。实际上,她就躲在皮村的家里,关掉手机读张岱的《夜航船》。而在去年《劳动者的星辰》出版后,她主动地承担起接受媒体采访的工作——其他工友起早贪黑工作太辛苦,而自己做小时工相对轻松,“每个人要承担每个人的责任”。她不讳言自己接受采访的真实心态,“如果(这本书)能多卖一点儿,咱们大家也能多点收入。”
文学小组组长付秋云坦言,对于工友们来说,写作的稿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生活的压力,但太不稳定,“要挣钱还是得老老实实地打工”。因此文学小组的讲座只在每周末的一个晚上进行。
“我们的书有点火,但大家的生活都平淡极了。”范雨素说。
即使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听到“作家”“文化人”等标签,她还是连连摇头。曾有活动邀请范雨素参加时,把她称为“民间诗人”,她却问能不能改成“农民工”。最后她以“《我是范雨素》作者”的身份出现了在活动海报上。她只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范雨素在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
图源受访者
“我就是喜欢文学。”范雨素的文学情节从幼年时萌芽。她六七岁就学会了自己看小说,八岁看懂了繁体字的《西游记》。少年时,古典小说、知青文学、外国作品,她把一切能找到的书籍都拿来读。在文学小组的成员中,范雨素是读过的书最多的人。
其他成员大多也曾在年少时短暂地与文学结缘,又在文学小组得到了第二次启蒙。月嫂王成秀只有小学文化,但就是小学课上那几首古诗让她深深着迷。加入了文学小组后,她以家政工视角写成的《高楼之下》也入选了文集《劳动者的星辰》。今年70岁的顶棚匠徐克铎,小学时没上过几节课,“十个字有八个不认识”,参加工作后才渐渐识字,对文学更是毫无概念。他迁居北京皮村后,和范雨素成为邻里,帮她照看过孩子。看到范雨素写文学作品,他也好奇,就跟着去听文学课,“发现老师讲的都是现实生活,能听得懂”,于是从零开始,现在已经“对文学入迷了”。

文学小组在上课
图源受访者
文学在青年小海的世界却远没有这么平和。“文学以前对我来说是星辰,现在就是沙子。”他有些忿忿地说。2016年,他还是流水线工人,但已经写了几年诗,“发关于工厂生活的牢骚”。他把自己的诗通过微博发给了音乐人张楚,张楚回复了他,向他推荐了皮村文学小组。就这样,29岁的小海凭着微博聊天框里一句遥远的指引,来到了北京皮村。
第一次上课,他迟到了一会,胆怯得没敢进去,就在外面听。上过课后,他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这里平等、开放、热爱文学的氛围正是他无比向往的。他就这样留在了创办文学小组的社会企业北京工友之家。
七年前,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组织”,立志要靠文学开拓一片天地。然而热度没有眷顾这位满怀理想的青年。以小海为主角之一的纪录片《我们四重奏》讲述了这群皮村打工青年们的生活,还入围了2020年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广受好评。不过影片最终未能公映,“还是挺遗憾的”。

小海剧照
图源:纪录片《我们四重奏》
七年后,回想起当年的豪情壮志,小海毫不犹豫地说“特别特别后悔”。曾经自己为了所谓的理想不顾一切,结果到现在一事无成,“还不如打工,谈个恋爱、结婚、生子,过平淡的日子。”心态的转变背后是年龄的增长、家庭的压力、同龄人的对比和创作的困顿——文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不过即便只是沙子,文学依然是他情绪的出口。他不打牌,也不打游戏,有空看看书,下班了有时在温榆河畔或皮村街上转转,隔三岔五在朋友圈留下一些诗句,期待着从灰暗平淡的生活里打捞起与众不同的那粒沙。给他的诗句点赞的,多是他来文学小组之后认识的朋友们。
工人中的“少数派”
对范雨素来说,文学从不“高高在上”,反而对于工人群体而言,“文学是最近的”。这与她早年在老家当了八年民办小学教师的经历不无关系。根据教育部2022年数据,基础教育的普及,让中国的识字率从1949年的20%提高到了2022年的95%以上,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也达到了99.9%以上。“几千年的历史中,劳动人民和文学都是有距离的”,但“现在每个人都能读书”。
工友们的文笔未必出彩,但范雨素觉得“真实的感受”是比文笔更重要的事。如果不真实,“写的再好也跟塑料花似的”,而文笔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曾经文学小组的工友让她推荐文学作品,她推荐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浩然的《艳阳天》,都是以底层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
的确,相比于乐器、绘画等其他文艺爱好,阅读和写作的成本更低。但即使“文学是最近的”,范雨素也从不与文学小组之外的人主动谈起文学,因为“那样会让人觉得奇怪”。在容纳了几万的人口的皮村,皮村文学小组里活跃的成员不过二三十人。在皮村的主街走访,不论是住了七八年的水果摊摊主,还是新搬来的年轻白领,都不知道皮村文学小组的存在,也对“范雨素”这个名字没有印象。对于更多的工友来说,文学仍是个陌生的词汇,《我是范雨素》引发的一系列热议其实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视线。

皮村街景
图源受访者
在范雨素看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乐趣”,对于热爱文学的工友们而言,文学小组是他们为共同的爱好抱团取暖的地方。然而文学小组的出现,却是个幸运的偶然。
组长付秋云是个90后姑娘。她来到皮村前在苏州打工,空闲时也在公益机构做志愿服务。2010年,她听说工友之家有公益电脑班可以参加,就来了北京,并最终留在了这里,为工友们服务。她在皮村成家,如今有了两个孩子。虽然接触的大多数工友年龄都比她大,但大家都叫她“小付老师”。

文学小组电子刊物《新工人文学》第9期封面
图源:“皮村工友”公众号
2014年,付秋云注意到有些工友常去图书馆找文学作品看,就有了创办文学小组的想法,“问了五六个工友之后,就坚定要开”。但大家都没有文学基础,招募文学老师来为工友们上课的需求就自然出现了。
能讲文学的人大概不少,但是愿意每周驱车几十公里来京郊讲课的,确实没有几个。其中有水平又能被工友接受的就更加难得。好在张慧瑜的加入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他是北大中文系博士,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工友之家公开发布招募志愿老师的信息后,他是唯二的报名者之一,而最后只有他做起了指导老师,一干就是9年。范雨素觉得,慧瑜老师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渊博的知识和不懈的坚持,更在于他与工友们相处的方式,那种“让人感到很平等的人格魅力”。
在张慧瑜的课堂上,工友们觅得宝贵的轻松和尊重,这正是他的课能够留住工友们的原因。他带着工友们赏析文学经典,但不拘泥于文学理论,而是结合工友们的现实生活,让工友们畅所欲言,谈自己的想法。即使有时讨论跑偏,大家聊起生活中的故事和感触也没关系。张慧瑜更鼓励他们动笔写作,每节课都有作业。最开始的课上只要交了文章他就会送一本书。这份鼓励和热忱让范雨素等小组成员们感到“不交的话对不起老师的付出”。

张慧瑜在皮村上课(右一)
图源受访者
于是,既不懂理论,也没有经验的工友们就从“写皮村”开始——起初有的工友只写三五十字,还有的交上来没辙没韵的打油诗,但张慧瑜还是认真地阅读点评,鼓励他们继续写下去。工友们大多不会电脑打字,于是就手写文章,再由付秋云敲进电脑,后来还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我是范雨素》便是如此诞生。事实证明,他们“聚沙成塔”的办法成功了。
倘若没有工友之家的努力,没有张慧瑜的加入,文学和工友们之间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正是他们让文学变得距离工友确实“很近”。但即便“很近”,文学的引力依然有限。
虽然这些年来皮村的租客中有了越来越多年轻白领,但文学小组却少有年轻的面孔加入。文学小组的成员大多人到中年——小海今年36岁,已经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付秋云意识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她承认,要争取年轻人的注意力,书籍难与手机抗衡。文学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出生于60、70年代,由于家庭条件和时代等多方面原因,不少人早早中断了学业外出务工。虽然几十年来忙于生计,但心中对于知识和文学的向往难以割舍,这份情结成为他们相聚在文学小组的契机。而对于从小就活在电子屏世界里的年轻人来说,那个植根于纸质媒介的文学世界已经和他们脱节了。作为时尚的文学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而今天这份时髦存在于短视频、游戏、社交平台……谁愿意静下心来读书?这是文学小组面临的现实问题。
比文学更重要的事
纵使范雨素年少时就热衷阅读,但让她与文学小组结缘的契机却与文学无关,与生活有关。
2014年,她和两个女儿住在皮村的出租屋,彼时工友之家所在的大院里有一片空地,皮村孩子们平时在那里相聚玩耍。范雨素要接女儿回家,近水楼台,也就知道了工友之家和文学小组的存在。加入是“出于好奇”,而让她坚持留在这里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听了几次课后,她发现张慧瑜老师“和人没有距离”,和她想象中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范雨素心怀感激,“觉得老师上课不容易”,就交上了第一篇作文。

工友之家彼时所在大院
图源受访者
在创办文学小组之前,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工友之家,已经面向工友群体开办过诸如英语班、吉他班、电脑班、家庭教育讲座等等课程,但这些小组存续时间大多不超过一年。背后的原因既有工友们巨大的生存压力,也有老师们不稳定的讲授风格和意愿。所有人都没想到文学小组能走得这么远。
工友之家创始人之一王德志说,当时成立文学小组“也没太当回事”,是张慧瑜老师坚持不懈的付出“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位专家学者把工友们初出茅庐的习作当做作品认真点评,这本身就是莫大的鼓舞。
文学小组,更多是以文学爱好之名,创造了一个“没有歧视”“没有压力”的松弛空间。在这里,大家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把大家私人领域里的焦虑和困惑带到了公共空间”,这是比文学更重要的事。
范雨素做育儿嫂的这些年,不乏自尊受挫的时刻。她总是以外人的身份进入雇主的家庭,永远被人所戒备,从未被真正接纳。有一次她过年回家,女主人却要求检查她的行李箱,发现了她行李中的三本书,范雨素不得不解释这是她自己买来读的。还有的时候,她跟雇主去亲戚家里吃饭,雇主的亲戚却递给她一双一次性筷子。她在这种时候“就会有被刺痛的感觉”。

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展览
“北京有很多城中村,这些城中村里面会有很多个范雨素,很多个郭福来”,王德志相信,文学小组不应该是属于皮村的一枝独秀,而是“遍地开花才好”。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数据,我国有超过2.9亿的农民工群体。这群规模庞大的新工人,却往往在舆论空间中失语,即使受到关注,他们也常常是被表达一方,鲜少能够为自己发声。范雨素、余秀华、许立志……每一个新工人与文学相遇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关注,是因为他们不大符合社会对“农民工”的想象,只是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就显得格外特殊。而这份观看者眼里的特殊,背面也许正是被观看的新工人群体受到压抑和忽视的常态。
诚然,对生存尚且艰辛的新工人群体而言,对物质生活的关心是第一位的,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切,那么恐怕我们永远要为范雨素们啧啧称奇了。
底层打工者在城市里所感受到的冷漠和孤独,该如何疏解?在范雨素的故事里,她一手捧着书,读她爱的文学;一边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故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我是一个创造者”的自我价值感,和工作中机械重复的劳作有着本质区别。
正如《劳动者的星辰》的腰封上,范雨素写下的宣言,“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
参考资料:
[1] https://www.moe.gov.cn/fbh/live/2022/54618/
[2] https://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75/
[3] https://www.gov.cn/lianbo/2023-04/28/content_5753679.htm

2023.08.14 13:45
05
2025.09
05
2025.09
09
2025.06
 28:32
28:32
2025.06.19 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