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2021.04
早晨8点,吴昊戴着口罩、护目镜快步走进理科楼。北京的春天对他并不友好,由于严重的花粉过敏,办公室里的空气净化器必须始终以最大功率运转。三个大书柜、三张大白板和三台显示器,是他日常工作的标配。
“我是一个很放松的人。”吴昊从沙发边拿出一双拖鞋换上,“在办公室嘛,怎么舒服怎么来。”
他换掉口罩、打开电脑、烧水煮茶,放松地坐进扶手椅。“这是清华109周年校庆的‘清云沱茶’,清华对口帮扶云南南涧推广的普洱茶。”吴昊指着刚刚添满的杯子说,“感兴趣的话就一人拿一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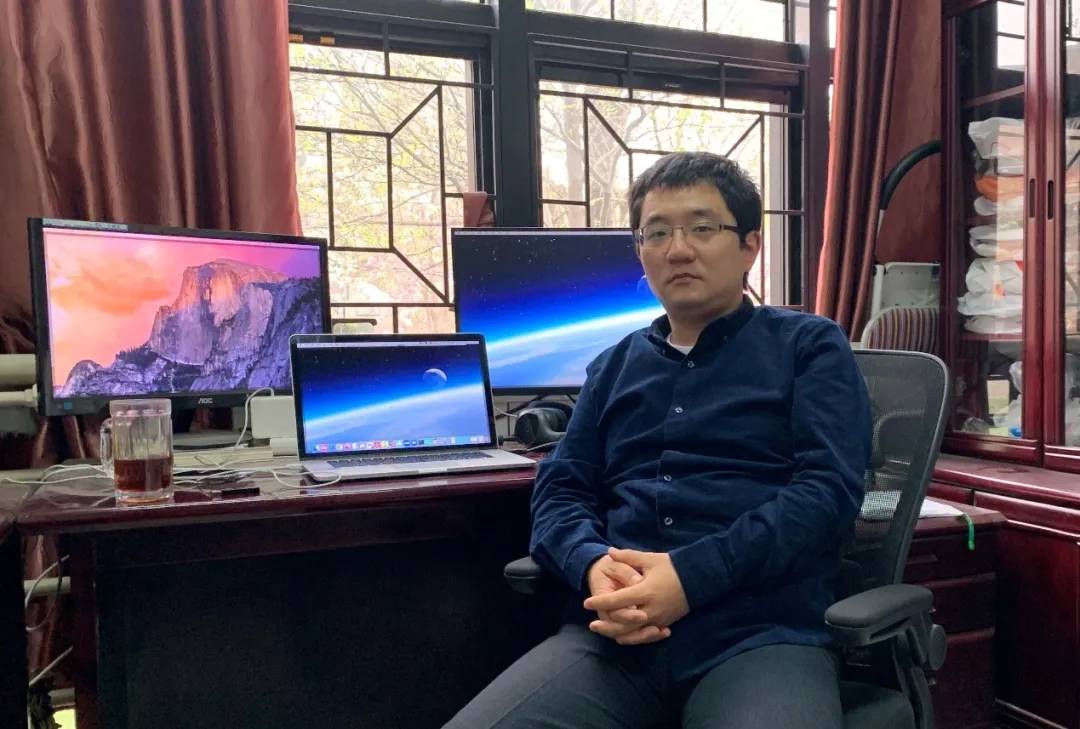
迷茫时刻
吴昊在清华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的中国,是WPS、CCED和KV300大行其道的时代。计算界英雄辈出,求伯君、朱崇君、王江民各领风骚。在高中写过杀毒软件、搞过数学竞赛的吴昊,彼时刚刚获得学校推荐保送清华的资格,正热切期待着自己驰骋IT江湖的未来,剑指清华计算机系。
“结果半个月后,招办那边打来电话,信息学竞赛没拿奖。”他无奈地说,“只能调剂去数学系,你去还是不去。”
吴昊想,那有什么办法呢,去就去呗。就这样,他拿着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了在数学系摸爬滚打的二十年。
大学的前两年,是吴昊迄今为止的人生谷底。高等数学的思路与数学竞赛截然不同,摸不清正确学习方法的他一筹莫展。大一那年,为了拯救自己“physically要挂了”的数学分析成绩,吴昊花费大量时间刷了吉米多维奇(指Б.Д.吉米多维奇所著《数学分析习题集》),却依然在期末考得惨不忍睹。
“后来我意识到那是工科学生应该刷的,数学系看重的不是计算,刷了没用。”他说,“那门课我真的是被捞上及格线的,我很感谢那位老师。”
找不到灵感、听不懂、学不会,课上老师过高的水平让他无法适应,课下自学又找错了参考资料。大一那年,保送进清华的吴昊在数学系的九十多人里排八十几名。
强烈的挫败感和自我否认如同大山般压来,吴昊“只能顺着来”。只要写完作业,他就逃出教室、逃出数学系、也逃出清华,试图在难以领会的数学知识以外,找到能填满生活的寄托:他骑车,在清华和香山间来回折返,在车水马龙的四环上反复兜圈;他看话剧,赶上了孟京辉如日中天的年代,在《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切·格瓦拉》里,吴昊感觉自己的心灵被填满了。“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说。
逃避、顺性、释放,再到反思,是吴昊应对强烈自我怀疑的开解方式。在最迷茫的时候,为了“寻找真理”,他大一、大二的暑假都没有回家,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到晚地看书——什么书都看,无论哲学、科技、文化、历史还是军事。
吴昊最喜欢的是科学史和科学家传记。百年前的科学巨擘们在桌边侃侃而谈,万物演变、宇宙生衰,无上的真理可能就诞生在他们茶余饭后的谈笑之间。“好像坐着聊天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吴昊说,“这就是我理想的人生状态。”

“人生的轨迹是无法控制的”
让吴昊踏上理想人生轨迹的机会来得并不晚。他的“翻身”始于大二春季的“数学规划”的期末考试。“复习时学霸都认定老师会重点考证明题,而我傻乎乎把算法题也给刷了,结果老师重点考了算法题。”吴昊说。
从高中开始痴迷算法的他,在考试结束前半小时便已早早做完了所有题目。老师宣布延长时间,吴昊站起来提前交卷,用行动向同学们宣誓:“我的假期从现在开始!”
那场考试里,吴昊是第一名。
如果说“数学规划”的翻身之战是他心态好转的契机,那么“数值分析”、“偏微分方程数值解”则终于把物理、计算机与数学联系的可能性带回到吴昊眼前,让在迷茫中的他第一次有了“以后就做这个了”的念头。
在吴昊看来,基础科学的研究是个很看“眼缘”的事情,有些课就是学不懂、“崩溃”,有一些就是“学得爽”、“有感觉”,他用电脑游戏“三国志”中的隐藏属性“相性”来形容这种微妙的区别。看到方向的吴昊,开始刻意挑选那些与他“相性相合”的课程。在之后的几年里,他选修了不少培养方案以外的算法课、物理课。
命运又一次眷顾了他。临近保研,吴昊的研究生导师被聘为清华数学系第一位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导师希望优先招收有物理和计算机背景的学生。数学系符合条件的学生寥寥无几,吴昊顺利通过考核,成为导师在清华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跨进了应用数学的研究之门。
“我的人生就是在自信心爆棚和被打击之间不断地循环。”吴昊说。他认为自己总有一种“谜之自信”,即使在本科阶段同门的成绩就比他好,这种自信还是让老师把比较困难的问题交给了他。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吴昊又一次意识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
前几年的研究进展缓慢,眼看着同级同学已经发表论文、顺利毕业,吴昊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博士四年级时,迟迟没有满意成果的他去了美国,脱离原有的社交圈,跟在导师身边静心研究。
“我在那里遇到一个很厉害的师兄。”吴昊回忆道,“他跟我说,你现在做的这个课题,我都做不了。”
意识到能力局限的他及时转换了方向,在导师和前辈的悉心指导和前几年不断积累的共同作用下,找到合适选题的吴昊厚积薄发,终于取得了突破。
“终于还是顺利毕业了。”他自嘲道,“不过还拿到了优秀博士论文和优秀博士毕业生。”
直至今日,吴昊依然时常在莫名自信和自我否定两种状态中不断切换。他提到一种名叫“冒名顶替综合征”的心理学现象,意思是人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取得的成绩不是自己应得的,甚至害怕别人发现这一点,并为此感到深切的自卑。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吴昊说。神迹般的灵光一现或者波澜壮阔的大起大落,是属于少部分人的神话,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失败、“跌到谷底再重新爬起来研究”的努力和一点点幸运,像构成大多数人的生涯一样,构成他的生涯。
二十年前的本科生吴昊被困在自信与失落的循环中时,会通过“骑车刷四环”来逃避现实,他会“感到浑身疲倦、大汗淋漓”,然后“冲个凉、睡一觉,让自己实现重启”;二十年后,已经成为清华数学系长聘副教授的他,平静地接受了自己依然需要经历心态起伏的现实。
“现在年纪大了,身体经不起那么浪。”他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赘肉,说,“我还能在西操连续跑上25圈,不过更喜欢去邺架轩看一下午书。”但现在多了一些无奈:“只是晚上得熬夜加班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吴昊很喜欢讲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故事。这位“传奇人物”拥有相当神奇的人生经历,从成绩很差到考上研究生,最后回到母校当上教务长;他的同事,志在理论物理,却在一场重要的选拔考试中与李政道先生的学生们狭路相逢,后者包揽了当年的前三,他只能转去学天体物理。
“这位同事后来成了台湾清华历史系的教授。”吴昊复述了讲故事的那位教务长的话,“一切都不是生涯规划规划出来的。所以,人生充满了不确定,你只能努力。”
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吴昊调整自己生活姿态的不二法门: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合理评估自己的实力,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决定去留,不让遗憾左右自己的生活。

现实派理想主义
微博段子说,人生宛如迪士尼乐园里的过山车,只存在三种状态:上下起伏、原地打转、上下起伏并且原地打转。吴昊是气定神闲地接受人生上下起伏的老手,不过比起原地打转,他更钟爱于跟随好奇心“四处打转”。
学生时期的他,便已将“兴趣”作为选课的重要标准。在专业相关课程以外,他特别提到了钟笑寒老师的“经济学原理”和李强老师的“社会学”两门课。“我意识到认识世界的方式除了理工科的思维,还有讲求效率的经济学、讲求公平的社会学。”吴昊说。
直至今日,吴昊依然保持着广泛阅读的习惯。他说自己最近在读的书“比较小众”,是《苏联高层决策70年》,但聊起其中内容时,吴昊的兴奋劲儿半点不减。“你们能想到吗?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的时期就已经提出了。”他说。
如今吴昊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学者,但他的好奇心始终如故。他会习惯性地浏览Nature, Science上的最新文章,即便绝大部分都看不懂,但他“就是喜欢瞎碰”。“万一那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呢?”,而且“我特别喜欢那种开大脑洞的论文,科学家的想象力比小说家要丰富多了”。
博士毕业以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转变研究方向,终于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几年,他专注于应用数学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都非常重要的“最优输运理论”。虽然其中理论分析并不是吴昊擅长的方向,但他多年的研究经验和对相关领域的充足了解,能够支撑他“找到有趣的应用场景”,让学生能够放手一搏。
“我会找几个‘不怕死’的学生来钻研。”吴昊笑称,“细节部分我不会算没关系啊,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做得很好。”
他停了一会,又严肃地说:“不过,很偶尔的情况,我也得去兜个底。”
吴昊办公室里的沙发背面墙上贴着一大张白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公式和推演过程。他喜欢带着学生围在白板边讨论论文中推导过程的精髓,然后不断追问他们。学生会因此发现自己忽略的细节,而吴昊会获得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并确保了他们最后得出的几条结论经得起推敲。
吴昊喜欢从最简单、最本质的角度把握困难的问题。抽丝剥茧、步步简化的过程,让他觉得“很爽”。
“我会push学生把他们研究的问题,用微积分的语言讲讲看,用离散的方式讲讲看。”吴昊说,“最好能讲到让高中生听懂——其实是让我能听懂。”
多领域的广泛了解是吴昊自己的研究准则,也是他对学生的期待。“用网上的话来说,你不喜欢我的方向,我可以改。”吴昊说,他会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点找合适方向,寻找与自己熟悉领域重合的部分,同时寻找更厉害的专家,为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
吴昊特别提到了他现在课题组里的一名博士生,称他水平很高,“反正比我厉害多了”。在他直博前半年迅速完成两篇论文后,吴昊“禁止他未来两年继续写文章”,而是让他去广泛阅读该领域里所有的研究成果。“还要读上几十万行代码,他读得很开心。”吴昊说。
这番坚持下来,那位学生已然成为课题组的顶梁柱。每次组会讨论,一旦面临新的问题,那位博士生就会举手,说类似的问题我在哪几篇文献中看到过,并迅速将主要结果整理出来,大大加速了课题组的工作进程。
“我要把他培养成‘藏经阁僧人’一样的角色。”吴昊说。
自身读博五年、当青年教师的经历让吴昊深知顶着压力研究是什么感觉,他不期待学生“上来就去啃硬骨头”,而是相当现实地帮助他们在攻读博士初期就发一篇小论文。在确保自己可以拿到学位、顺利毕业的基础上没有压力地做大问题,对学生的成长最有帮助。根据他的说法,这叫“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谈理想主义”。
不过,在现实的考量之外,理想主义毕竟是他的人生底色。
吴昊的微信头像是一个“戴森球”,一种科幻作品中常常提到的,先进文明用大量卫星包裹起整个恒星而形成的巨型人造结构,这样可以获得恒星绝大多数或全部的能量输出。通常认为,观测到“戴森球”就意味着观测到了外星文明,人类视野的疆域将前所未有地广袤。
吴昊一直很喜欢科幻,“以前在bbs上和刘慈欣聊天”。他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低温核聚变和高温超导——两个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但至今悬而未决,甚至连解决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的重要问题。
“反正我现在是长聘副教授,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吴昊笑称,“等哪天真的完全衣食无忧了,我一定要看看这两个问题。”
“你我皆凡人”
知乎上曾有关于吴昊的讨论,说他扬言在考试里“想出多难的题就出多难的题”。回答里却是学生清一色的维护:“吴昊老师是个好人,他只是嘴上那么说说。”
吴昊给本科生上的课是“复变函数与数理方程”,面向电子系开放。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他为了融合式教学的效果绞尽脑汁,在授课时不厌其烦地切换摄像头角度和屏幕共享画面,尽力确保线上或回放能和他设想中的授课步调严格一致;为了达到最好的收听效果,他与教学设备斗智斗勇了将近一个学期。
“那个麦克风靠近黑板就会啸叫。”吴昊不止一次地抱怨,“实在是太吵了。”
偶尔,学生能在上课时看见他突然关掉录像功能。每当这一动作出现,全班同学都会突然“抖擞精神”、充满期待——“这意味着吴昊老师要开始讲段子了。”
课上,吴昊最喜欢的保留节目是“数学家族谱”。数学领域的师承记录相当清晰,沿着“博士导师的导师的导师”不断向前溯源,能够很容易地与大师建立联系。
吴昊的“学术祖先”指向希尔伯特、欧拉、高斯、莱布尼茨,每个都是数学史上光芒万丈的名字。“我特意把儿子的英文名起成Isaac,这样我就能和欧洲两大学派都沾上边了。”他用这一句话为这个保留节目收尾,很得意的样子。
作为同样在数学系挣扎过的“平凡学生”,吴昊知道怎样调节课堂气氛,更清楚怎样为“想好好学”的学生提供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复变函数与数理方程”课堂上的学生,常常会听到吴昊对知识的难度作出果断判断:复变函数更成体系,一气呵成,讲起来听起来都简单;数理方程知识点多,技巧灵活,学习起来难度会更大。
“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难度的评估,要告诉他们这个问题难在哪儿、本质的困难是什么。” 吴昊愿意用数学语言一样简单、精准的表述去接近问题的本质,他喜欢“假设一切条件都是好的”,把复杂的表象剥除,直击数字、逻辑、定律运转的最根本脉络。然后再点到即止地介绍“条件不那么好时,数学家会怎么处理”。
上课从不点名签到但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作业和习题课的问题和答案编排得整整齐齐发送给所有学生;在课程中设置学有余力者可以挑战的难题,也带领所有学生好好掌握后续学习的必备技能……“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就可以通过”,是吴昊设置难度的准则。
自身并不一帆风顺的学习经历,让吴昊相信自己绝对能理解大多数学生的纠结、自我否定和迷茫。他能注意到“有些学生的学习其实是很艰辛的,他们没有轻松地理解课程内容,但的确努力过了”。
不可逃避的困难时时浮现,接受它,但不放弃挑战它,是吴昊一直以来“顺性中带一点不屈”的人生态度,也是他希望在学生身上再次看到的东西。
年轻时的吴昊曾被讲述早期党史的著作《苦难辉煌》深深震撼。那是一部真正苦难的集合,许多“牛人”曾是更早的“牛人”的部下,漫长的历练中有无数真切的悲剧;他感到“红军很多的决策都像开挂一样”,那种摧枯拉朽的战斗力亦是在长征中练就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苦的了。”他说。
在吴昊看来,极端的苦难使红军脱胎换骨,平凡的苦难则是平凡人生的常态。
“人往往会放大悲剧在自己身上的严重性,认为自己是最惨的。”吴昊说。你我皆凡人,正因为任何人成长过程中必经的失败和妥协,他也都经历过甚至仍在经历着,他才更加坚定地相信寻找、思考、反省、调试这样平淡的过程,才是人生永恒的状态。没有悲剧的生活,只在童话中存在。
“你知道吗,我近几年发觉自己能够看得进去那种小人物、慢节奏的电影了。”吴昊说。相比于那种全明星、大制作,这类片子让他感觉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2025.12.16 15:15
16
2025.12
16
2025.12
16
2025.12
 28:32
28:32
2025.06.19 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