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2021.06
1996年,杨扬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在那个年代,“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言犹在耳,生物是真正的热门专业。
然而,真正开始本科的生物学学习后,杨扬恍然发觉,自己对“生物学”的想象,和现实“太不一样了”。
时隔21年,她仍然忍不住感叹:“我们当初真的学了很久的数理化。”
从“被劝退”的生物学生,到“教历史”的生物教师,杨扬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想在课堂上成为一名讲故事的“故事家”。

写故事
杨扬本科就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
在她的记忆里,大学学习生涯的很大一部分,被数不清的“有机、无机、物化、分析”占据。化学课又多又难,她最头疼的“无机分析实验”更是被安排在了上午第二大节这个影响吃饭的关键时段。
“实验做到一点都算早的,经常饿着肚子做实验,做不好老师还不让走。”即使勉强完成了实验操作,一旦产物不合格,老师马上就会垮下脸来:“你必须得给我重做!”
最终把杨扬从生物化学领域“彻底劝退”的难忘经历来自某次蒸馏实验。走出实验室,一阵风刮过,杨扬突然感觉“脚下特别凉”,赶紧往下一看,自己的鞋子和裙子竟然破了好多洞,而且破洞还成溅射状分布。
“那天实验用到了腐蚀性很强的硫酸,估计是某组同学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溅出来了。”她说,“当时还挺后怕的,因为鞋子袜子都破了,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杨扬对生物专业的真正兴趣始于当时的“普通生物学”。当时授课的老师擅长动植物学,上课不爱让学生死记硬背,喜欢在下午的课上带杨扬和同学们去校园里漫步,鉴定满园的各种植物,捕过蜻蜓和蝴蝶。她至今仍对野外实习时,老师带着他们出海看各种海生生物的场景记忆犹新。
升入高年级,生化、分子、微生物这些微观生物学的课程,却越来越让她感到“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
九十年代末,分子生物学还处于兴起阶段,那会儿给他们讲分子实验课的老师很多实验自己也没做过。当时杨扬非常期待的一个“大项目”,就挺让她失望的。那次发酵实验,老师没让他们做重要的操作,只是让大家轮流守着那个大大的发酵锅,偶尔看一眼温度和pH值就行。她觉得,这“不能算是做实验,顶多算是站岗放哨”。
没意思,很无聊,所以杨扬从厦门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打算继续进修生物研究生,甚至干脆避开生物开始找工作。据她回忆,毕业那会儿就业形势还可以,家长也没有给她找一份高薪工作的压力,她在毕业选择上有许多自由。
就这样,杨扬一口气从厦门回到家乡北京,找了一份看起来和生物毫无关系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工作。
当时的主编招她时说,因为生物学现在很热,所以他希望找一个有生物背景的人——就这么误打误撞,杨扬当上了记者。
新闻、采访,这些都是杨扬完全陌生的领域,她接触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聊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的故事。不过,因为“主编的期待”,她主要接触的还是生物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
生活的转折就从她的一次采访开始。
当时,杨扬采访了初建阶段华大基因(现国内著名生命科学科技前沿机构)的一位科研工作者。他告诉杨扬,因为生物实验周期太长,公司创立初期其实一直在亏钱。当时杨扬看着一屋又一屋的实验小鼠,非常好奇他们如何在亏损状态下坚持下来。那位前辈就告诉她,现在全世界的生物技术研究者都在“蓄势待发”,技术井喷很快就会到来,中国在生物领域的发展机会非常大。
前辈说到的“在美国实验室能看到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东西”,还有测序、抗体、疫苗、药厂等等词汇,杨扬似懂非懂,但是她真的被感动了,也被激励了。
“所以,我就又跑到美国去读博了。”
匆匆“考G考托”, 匆匆写好一堆海投申请,匆匆把一堆letter(推荐信)拿给老师签名,就这样,在2001年的夏天,杨扬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

遇故事
2001年,刚到美国圣约翰大学生物系读博的杨扬就接到了微生物实验课的助教任务。
与国内的安排不同,她所在的大学要求研究生负责理论授课、器材准备和实验指导的全部过程。和杨扬合作的助教见她初来乍到、毫无经验,故意把最难讲的内容都分给了她。
“一开始绝对没有觉得自己有上课的天赋。”杨扬说,“而且我那时也真的不会讲课,只能‘生背’讲稿。”在申请季紧赶慢赶考完托福的她,自认英语只有“半吊子”水平,一上来就要教美国的大学生,心里根本没有底。
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杨扬跟台下的学生只差了一两岁,甚至有学生表示,大家都以为她“还是高中生”。因为看起来过于年轻,同学们对杨扬并不敬畏,在她犯错时嘻嘻哈哈,在她下台指导实验操作时不断插嘴,甚至频繁打趣:“老师你那个单词的发音不准。”
“我以为我会哭,但其实没有。”杨扬说。第一节课上完,她的自我评价是“非常糟糕”。
第二节课上,杨扬进行了一场小测验,现场批完以后,一大群学生冲上来围住了她,要来为自己的分数讨个说法。
“当时我真的有舌战群儒的感觉。”杨扬操着一口磕磕绊绊的英语,左劝劝、右劝劝,终于从课上“逃生”了。
所幸熟能生巧,随着担任助教的次数增加,杨扬发现自己“讲多了就知道该怎么讲了”,渐渐适应了教学工作。加之美国课堂氛围包容,老师、同学都将犯错看做稀松平常的事情,师生关系相当融洽。教授在同学实验失误时会一个劲儿地夸:“Perfect!我们换一个再接着做!”在杨扬讲错的时候,同学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相反热情地鼓励她:“Come on!没关系!”甚至那些在课上开她玩笑的学生在结课之后,还会主动跑到实验室来找她聊天。
杨扬很感谢在美国的这段教学经历。正是这种包容的氛围给了她不断试错的机会,让一个“赶鸭子上架”的代课老师逐渐积累宝贵的经验,并萌发了对教育的满腔热爱。
2008年,杨扬在美国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攻读博士后学位。那个夏天,她不经意间发现,自己院里的美国教授们都在熬夜收看北京奥运会比赛,并不住地与大家分享观后感:“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之前从不收看体育节目的杨扬也打开了电视机。从祖国传来的转播画面,不仅“shock”了整个美国,也震撼了自2001年便出国深造的她。
“外出留学之后,根本不知道中国发展得竟然这么快。北京奥运会时,仿佛整个美国的记者都跑到中国去了,电视上关于中国的节目特别多。”
祖国的飞速发展彻底激发了杨扬完成学业后回国工作的欲望,恰好她的丈夫也正有此意,两个人一拍即合:“回就回!”
2012年,杨扬博士后出站,回到北京寻找工作。当时的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原本教授基础课程“现代生物学导论”(下文简称“生导”)的老师即将退休,学院正在寻找接替人选。机缘巧合下,杨扬参与了面试。
“试讲课我做了四十五分钟的准备,到现场讲了十五分钟,他们就让我通过了。”
就这样,杨扬重新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北京,开始了“生导”课的教学工作。这一上,就是九年。

讲故事
入职清华后,杨扬将她钟爱的包容氛围带到了“生导”的课堂上,这一次,她成为了主导者。
作为一门任选课,“现代生物学导论”的学生来自各个院系,背景各异、学科基础参差不齐。为了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杨扬在课前准备了知识密度很高的预习课件,并匀出上课时间仔细介绍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在课后又为有余力的同学提供涉及学科前沿知识的扩展内容。
“只有学生经历了独立‘dig’的过程,才能把一个生物学过程真正弄明白。”杨扬说。她始终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无论是平时作业还是期末考试,“生导”都不强调知识的死记硬背,而是考察对概念的理解、延伸和拓展,最大程度地兼顾了水平不同的学生。
在混合式教学小课堂分组搭DNA双螺旋模型,在大课堂上同学合作用肢体语言模拟动作电位的过程,在课后布置作业用彩泥模仿DNA重组过程……抽象的概念就这样通过杨扬别出心裁的课堂设计“活”了起来。
兼容、自由的教学风格也为杨扬带来了“意外之喜”。
她回忆起自己在以前讲DNA的时候,曾提到DNA双螺旋结构在生物体内的水性环境里是稳定的,这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下课后就有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冲上讲台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从物理学的角度讲说不通”,然后写了一黑板的公式给杨扬解释。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她问住了,杨扬只好表示自己听不懂,并对那位同学说:“咱们真是有知识‘gap’”。她想起生院的王宏伟教授实验室正在做生物物理学相关研究,推荐他去“问问看”。这位同学果真去拜访了王教授,还在王教授那里完成了自己的毕设。
这样的例子在生导课上并不少。同样来自物理专业的苏士千也在生导课上体会到了兴趣和收获带来的双重快乐。在做“新冠病毒”主题的大作业时,他对于流行病学的模型模拟和预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开始拼命钻研各种流行病学模型。“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各个官网上扒数据。”
杨扬说:“我希望大家在学习知识的过程当中,掌握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方法,以培养出一种思维习惯。”
杨扬对教学的期待并没有止于接手“现代生物学导论”。2013年,她在广泛听课、大量积累素材后,开设了全校通识课“生命科学简史”(下文简称“简史”)。相比更偏重生物学基础的“生导”,“简史”课的话题更接近于“生物历史”,面向所有学生,分专题介绍不同生物学领域的发展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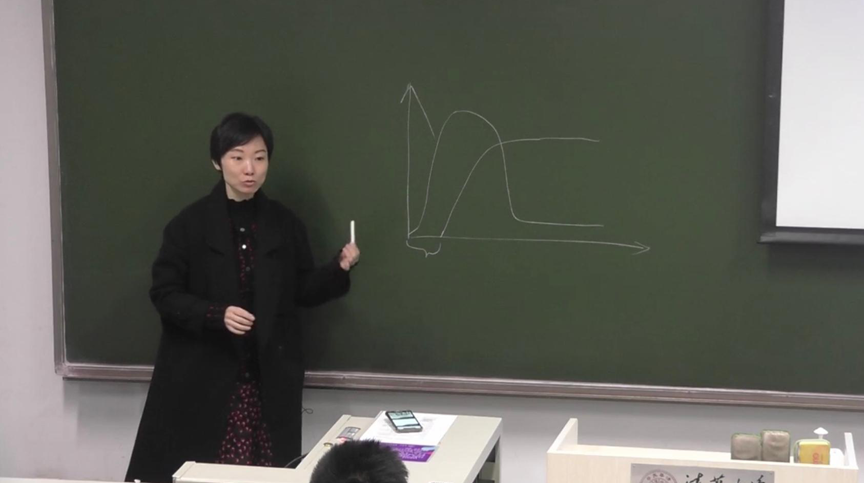
“我更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介绍生物知识。”
在圣约翰大学读博时,杨扬见到了她理想中的课堂设计模式。她的博士生导师在教授分子生物学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学科发展脉络、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生物学概念和知识框架的融合。在一节课上,教授讲述了科学家在噬菌体侵染流感嗜血杆菌实验中的不断失败是如何促使他们发现II型限制性内切酶的故事,杨扬听得津津有味,并且轻松记住了相关知识。
“(那种感觉)非常amazing!”她感叹道。
在清华任教后,杨扬开始站在老师的立场思考从什么角度来讲述能让大家更容易“把知识记下来”。亲身体验加上深思熟虑,她最终却选定了“历史+生物”的融合模式。“生命科学简史”的设计雏形愈发清晰。
有了想法的杨扬开始旁听清华现有的科学史课程。她很快发现,这些课程更多倾向于历史发展,内容很少涉及学科专业知识,即使提到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也只是在哲学意境下进行分析。“当时我就想,我要从理科的、生物学的角度,来开这么一门课。”
最初的“简史”课按学科细分领域设计大纲:这周讲遗传、下周讲分子,大家听听科学家的八卦,天南海北痛快畅聊,都觉得挺新鲜。但是随后杨扬发现,要想长期开设这门课,必须要让它更成体系。
在她的反复打磨下,课程渐渐从分科介绍变成了专题讨论:癌症治疗、疫苗争议、抗生素滥用……这些现实生活中与生物学息息相关的社会现象,成了杨扬手中打开生物学历史的钥匙。
“In God we trust. Others must have data.(我们唯信上帝。此外一切须用数据证明。)”, 在癌症治疗专题中,杨扬用这句话总结了科学家通过反复、谨慎的实验破除“根治术”疗效迷信的案例。科学精神、理性思维、实验态度,无论在哪个课堂上,她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讲授,为学生们带来更深、更广的视野。现在,《生命科学简史》已是清华大学首批通识荣誉课程。
在课上,杨扬着迷于和年轻人进行思维碰撞的过程。她尽可能压缩自己的讲授内容,把更多时间留作自由讨论,把课堂的主导权转交给学生们。正在上简史课的周明德说:“这可能是我目前上过的分组讨论最多的课。”她和学生从进化论聊到达尔文,从达尔文聊到种族主义,从种族主义聊到更深层的哲学命题:一节课就像从大树的树干开始,向外生长出千枝万叶。

过,比起在课堂上的得心应手,作为生92班主任的杨扬在生活中常常也觉得自己摸不透年轻孩子的想法。“现在的学生见过的东西太多了”,她总感到自己的苦口婆心很多时候起不到好的效果。不过很快,回想起自己当年经历的杨扬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就跟我家长平常总是唠叨,但是我听不进心里去一样。”
“我的孩子上小学都不怎么听我的,难道我还指望你们听我的?”她说。
找到沟通受阻的原因后,杨扬开始在课上课下努力寻找新的交流模式,试图打破自己和学生因为“师生”关系天然形成的距离感。课上,她利用雨课堂弹幕和课堂节奏的巧妙融合,把学生的注意力从手机上吸引过来;课下,杨扬把“和生92的每个同学都聊一次天”列上自己的工作安排。
每次和同学们约饭,杨扬的“话匣子”一开,一顿饭常常吃上两三个小时。同学们会向她吐槽,自己和她当年一样有学不完的数理化,她也会向同学们抱怨自己家的两个小学生“真是难管”。
杨扬一直和年轻人在一起。她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她没有说的是,学生们朝气蓬勃,兴奋的眼神中带着迷茫,一如当年迷迷糊糊离开那座充满海风味道的校园时的自己一样。她的孩子和学生还在苦思冥想人生故事的开头,而杨扬正在奋笔疾书。
她的故事写到高潮了吗?翻阅自己曾经写下的章节,杨扬觉得,如果有新的灵感,她一定会再次抓住。
“我可以做的事儿可太多了。”

2025.12.16 15:15
16
2025.12
16
2025.12
16
2025.12
 28:32
28:32
2025.06.19 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