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2021.09
“又来了。”这是现在的尹青(化名)看到与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的英文缩写,即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相关的策划时能给出的唯一反应。
恋爱故事、生存处境、反抗经历,作为一名“双性恋”,在确认性取向后的近十年里,她填写了不计其数的问卷,一遍遍讲述自己和挚友的感情经历、十二岁时的自我认同过程和来自身边的冒犯与偏见,直到终于对分享和交流失去了兴趣。
2019年,大一的尹青在“性别”主题的写作与沟通课上再一次见到了直人(指顺性别异性恋者)对LGBTQ话题的讨论。自由选题论文中,作者用耽美小说与相关影视作品作为描述“同性恋”的论据,怀着激愤悲悯的态度呼吁平权,却甚至不了解男同性恋内部的异质性。在尹青看来,这些对LGBTQ群体的包容、理解和分析,似乎成为“一种值得炫耀的、能够展示自身社会关切的事情”,而阅读这些讨论,总是带给她这个“局内人”微妙的错位感。
不过,对LGBTQ群体来说,“隔靴搔痒”的讨论毕竟有其积极意义。在无数次游行、无数次发声后,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ICD)大会决议,将“同性恋”这一条目从疾病列表中删除。联合国随即将5月17日定为 “国际不再恐同日”,呼吁人们关注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群体因性取向与性别认同而受到的恐惧、歧视、不公与暴力。
但尹青想要更多。
“现在不少友好人士关心、了解这些话题的态度,其实依然带有居高临下的‘解决困境’的立场。”尹青说,“就像在帮助流浪小动物。”
31年过去,在理解、宽容已然成为某种政治正确的今天,LGBTQ群体追问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在“不再恐惧”之后,“得寸进尺”的契机,是否快要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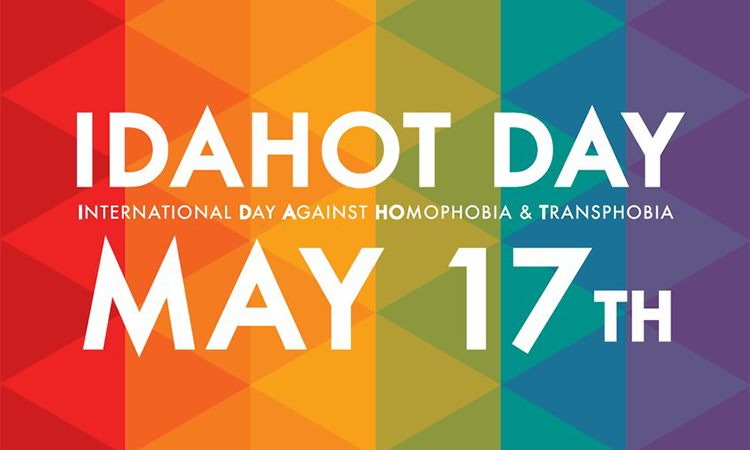
不再审视
早上八点,阿云(化名)拿着洗漱用具和衣物走进空无一人的盥洗室。紫荆公寓一览无余、没有隔板的淋浴间,只有在这时才能让作为MtF(male-to-female,即生理性别男性、心理性别女性的跨性别者)的她感到舒适。
三位直男室友曾见过她修眉化妆,也见过她的中性打扮:黑色长风衣、白色阔腿七分裤、小腿袜配白鞋。阿云留着及肩长发,如此穿着后,除了身型略显高挑以外,更像一名女性。
室友对此没有直白的反应,他们什么都不说,不闻不问,仿佛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刻意避开的眼神注视背后,潜藏着有意无意的窥探与审视。
同为MtF,这样的检视在飞鱼(化名)的生活中也未曾消失。
地铁站内,人来人往,形色匆匆的人们忙着赶往站台和目的地,人群之中,肩披长发、身着黑色长裙的飞鱼走向女卫生间。
一个从男卫生间走出路过的老人表示疑问:“错了,错了!”
凭借对自己外貌的每一个细节的熟悉程度,和对无数次出入女卫生间的经验的综合分析,飞鱼知道与自己进错了卫生间这一判断相比,老人看岔了眼这一解释反倒更能令人信服,便相信无需理会这呼喊,像是没听见一般,径自打开门走入隔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飞鱼一般自信,并能做到镇定自若。阿云表示:“跨性别群体恐惧使用卫生间,尤其是MtF群体,其中大部分人是很恐惧去女卫生间的。在没有无障碍卫生间的情况下,她们会选择忍住,直到回家再使用卫生间。”
恐惧去女卫生间的原因不尽相同,一些人觉得自己不够女性化,被指出乃至被注视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摆脱的麻烦,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在给顺性别女性平添困扰。
然而,更让MtF们更害怕的,是进男卫生间。以男性身份成长的MtF们,深谙男性所拥有的力量。“厕所暴力真的是一个我们很真实、很恐怖的一个事情。”阿云说。

事实上,时刻受到如影随形目光审视的,不仅是LGBTQ群体本身,哪怕仅仅在公开场合表示友好和支持,都可能感受到类似的局促。
5月17日当天,V(化名)在自行车的铃铛旁插上了彩虹旗。作为一名多次参与LGBTQ相关展览、口述史和访谈活动的志愿者,她将这一行为视作节日时自然且应当的表态。
“可我从宿舍楼一路骑到东南门,没见到第二辆类似的车。”V说,“彩虹旗多鲜艳啊,这么大一个,就会感觉所有擦肩而过的人都注意到了你。”
行人或多或少的侧目、迎面而来学生额外给予的关注、推车经过地铁口时站在门口的中年男子明显的异样眼神……“事实上很少有人会明显表现出不友好,”V说,“不会瞪你一眼,但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注视’。”
抵达五道口地铁站后,她把旗子收进了包里,凭借一路上的直觉,V担心把它继续留在车上,“一定会被拔走”。但在回程的路上,她犹豫再三,还是重新把旗子拿了出来,插进包的侧袋。在她看来,收起旗子的举动代表着某种退让,“好像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
“我以为它会安静地、不显眼地呆在那里。”V回忆说。直到她在路口等待变灯时注意到了地上自己的影子,赫然发现那面彩虹旗“飘得特别张扬”。
“我居然就这么一路招摇过市。”她说,“早上的所有不适、被审视的感觉,一下子全都回来了。”
在V看来,清华校内表达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公开表态者受到的注视甚至可能更多。校外的群体可能并不了解在“5·17”携带彩虹旗意味着什么,但在校内,她发现来来往往的同学们的目光里,多少带上了探究。
平心而论,这些注视可能并不含有敌意。但每一秒视线停留、每一次另眼相看,都让人鲜明地体会到,自己被识别出来、且正被标记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接受点评。
V这样描述她感受到的视线——“诶,这个人插了旗子。”
“仅仅是这样的审视,就足够让人不适了。”V说。

不再想象
审视的目光无法满足对于他者的好奇,目光无法触及之处,对于LGBTQ群体的想象填补了认知上的空白。
在传统的异性恋想象中,他们是病态与罪恶的。
在广州读书的小萨(化名),住在学校提供的六人间里,五名室友中,三名反感同性恋。室友曾见到过两个女生接吻,恶心且不适是她对此唯一的的印象。小萨也曾试图反驳,最终往往只得自己沉默下来。
小萨没有向室友表明自己的性取向。在她看来,这样的讲述是没有意义的。高中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境。那时的她想要证明自己的正常,在网络上查找各种资料,急切地讲述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努力想要洗刷掉身上的污名。
发现无法说服彼此后,大家会默契地不再谈论。但在之后的相处中,距离被刻意地拉大,再看过来的眼神中则多了审视和犹疑,沉默的芥蒂替代了公开表达的反对。
另外一些时候,想象会以更加公开且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
思修课上,五十多岁的男老师突然谈起同性恋的话题,接着便强硬地讲述着自己的厌恶: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就应该对这些人进行扭转治疗,电击疗法也好,呕吐疗法也罢,干脆去做变性手术也可以。
坐在台下的小萨,先是感到震惊,随之而来的便是愤怒。她想要向学校投诉。
“我当时连投诉稿子都写好了,但被爸妈严厉制止了。”说起这件事,小萨显得有些愤懑和遗憾。出于对自身的安全考量,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向学校投诉,这件事情也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如果投诉了会有什么后果,学校会不会处理。只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去做,那就真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现在回想起来,小萨依旧很坚定。

“男”与“女”的二元性别划分,“男友、丈夫”与“女友、妻子”的传统亲密关系,让大众对LGBTQ群体的认识总难跳出固有认知,充满个人经验下的想象色彩。这一想象在渗透在日常的话语当中。
一次分手后,尹青同另一位刚分手的直男朋友互相宽慰,知道尹青性取向的对方突然提出要尹青去追求自己的前女友,原因是难以接受她同其他男性在一起。“她是你喜欢的类型。”他这样解释。
“说实话我当时满脑子都是问号,甚至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回想起来,尹青仍然感到被冒犯,露出困惑的表情。
这样的话语,即便只是作为玩笑,也仍然会像一根鱼刺,哽在她的心里,令人不适。
更加具有冒犯性的问题也曾出现过。一次和关系不错的直男朋友聊起性相关话题,对方问到:“没有插入式性行为怎么可能愉悦呢?你们不如找个男性一起。”
酷儿学者J.哈勃斯坦(J.Halberstam,2005)曾提出 “酷儿时间性” 的概念。他指出,异性恋霸权通过特定事件给人生下定义、划分阶段,把结婚与否作为衡量个人是否成年或成熟的标志,把婚姻和生育描述为所有人的本能。LGBTQ群体难以通过结婚仪式满足相关社会期待和义务,他们的爱情则可能被认为是非正式的、残缺的和不正当的,是一种浅显而容易破裂的不稳定关系。
刻板印象的想象之外,对于LGBTQ群体关系的美化与浪漫化也同时存在,甚至在令人不适的程度上,后者更胜一筹。
很早就认知到自己是gay的大能(化名),对耽美作品并不感冒,他所认识喜欢耽美作品的人,往往是身边的直女朋友。
她们痴迷于两名男性之间的爱情,为刺激的情节心动、脸红、尖叫。“嗑死我了!”“绝美爱情!”“老公和老婆也太甜了!”她们这样高呼。
但在作品之外,她们从不会把从中获得的认知套用在LGBTQ群体身上,不关心相关的新闻,亦不会为这一群体发声。
对于耽美的爱好仅仅止步于虚构的爱情故事,更多时候吸引爱好者的,是各具特点的男性角色和更加平等的亲密关系模式本身。爱屋无法及乌。
即使并非主动了解,耽美作品的影响依然会无孔不入地渗透进LGBTQ群体的生活中。中学时期确定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滴滴(化名),会被班里喜爱这一题材的女生主动分享相关作品,点开app则会被推荐极具暗示性的影视片段,即便是刷微博看综艺,也会一不小心看到相关的视频。
“我会很厌恶耽美。”滴滴说,“明明同性婚姻关系不被法律所认可,这个社会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消费着同性恋群体的爱情。”
我国当下的影视作品中,出于审查的限制,剧本中往往不会点明主角间的关系,却会刻意地通过人物设定或情节对白,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同性间的爱情。
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创作主体与主流面向对象仍然是异性恋群体,这使得大多数耽美作品成为异性恋对同性恋想象与凝视的载体,而同现实存在较大出入。日本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佐藤雅树认为:耽美创作中的同性恋男性人物过于理想化,不符合现实,这类文本在大众中的传播并不利于改善同性恋社群的状况或增进大众对同性恋困境的了解。
“真正喜欢这些的并不是同性恋,而是那些对于同性恋有好奇心态的人,或者说是希望同性恋活成他们心中范式的人。”
滴滴觉得,如果你想要尊重和关心同性恋,就应当去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让公共舆论空间真正地去接纳这个话题,而不是将同性恋群体脸谱化,新瓶装旧酒,在同性恋的包装下继续加深异性恋关系的刻板模式。
刻板印象下,对于男同性恋1或0的识别,对于女同性恋T或P的划分,对于男性或女性二元性别的框定,本质上都是异性恋模式的再生产。LGBTQ群体真实的生活,并非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另一种异性恋模式,他们想要的,也并非耽美作品所带来的浪漫化想象或另眼相看。
不再限制
阿云对于自我的确认,本身是一个打破限制的流动过程。
记忆中第一次穿女装是在七岁,二年级,在一次回老家的时候,阿云偷穿了表姐的裙子。奇怪和焦虑的感受无法阻止她继续尝试,她开始在他人看不到的时候穿女装,换上衣服的她感到舒适与自由。
但在内心深处,阿云把自己当成异装癖,甚至是变态,那些难以对人言说的困惑,只能被偷偷埋在心里。直到18岁来到大学,“跨性别”这一概念给了她某种可能的答案。
阿云开始在网上买女装,学习化妆。宿舍里不方便,她就放假回家前在机场和火车站附近订酒店,或是在没有人的家里做尝试。
“我是因为享受这种打扮的过程吗?这种过程会给我带来性兴奋吗?我是更喜欢女装后的外表吗?”
尝试之后,她发现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于是她开始留长发,穿更中性的衣服。
直到一次同父母出去旅游,阿云在高速休息站上厕所的时候被人认成女生。她突然意识到:“我所渴望的,不是穿女装本身,而是这种社会认知。”听到“美女”、“姐姐”等称呼时,她感到自然和舒适。
困惑、探索、焦虑与抑郁后,阿云最终发现:自己想要的,不是穿女装,“我觉得我是一名女性。”

有关自身性别的重新思考进一步带来了对于性别议题的关注。
2020年底,阿云开始成为女权主义者,过去的她对此毫不关心。“对于女性来说,经历过苦难会给她带来很强的力量,我是反过来的,我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而是女权给了我力量。”聊到这些,她的叙述条理且坚定。
对于刻板印象的思考,支撑了阿云的自我认同;对于女性客体性的思考,也让她解答了在以女性身份生活时,所感受到不适的源头是什么。
作为男生长大,阿云曾经迷茫自己是否没有资格做一名女权主义者,是否没有资格完成跨性别的过程,直到她读到一名美籍日裔跨性别女性所写的《跨性别女性主义宣言》。
“女权是最有可能推翻父权结构性压迫的一场革命,我既作为LGBTQ的一员,又是一名跨性别女性,没有理由不成为女权主义者。”在阿云看来,这不仅是女性所选择的答案,也是LGBTQ群体的唯一出路。
只是,在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那里,跨性别的身份成为阿云被拒绝的原因。
每当她想在网络上加入女权小组时,总能看到“仅限生理女”“MtF(男跨女人士)别来碰瓷”等字样。在女权主义者的群聊中,阿云也曾听到过很多对于跨性别群体的排斥:“很多跨性别者只是心理认同自己是女性,对经历了很多生理问题的女性来讲非常不公平。倘若她们说自己是女性,会挤压对女性本就不友好的生存空间。”
出于生理性别的限制,MtF群体在理解女性经历上确实存在着某种成长历程所带来的隔阂。但这一隔阂并非不可破除,在和女朋友的讨论与相处中,阿云得以更加了解其他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虽然说我非常认可和理解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会对跨性别女性这么排斥,但这种排斥中还是带有巨大的污名化和歧视性。”提起女权主义者“排跨”的现象,阿云觉得可以接受,但还是会有些伤心。
一些人认为,MtF群体的存在加深了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阿云却有着不同的感受:跨性别群体本身也是很多元的。有人利用和加深性别刻板印象,以物化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并产生了影响力;但也有很多人,在努力挑战着性别二元框架。
“跨性别里很多是非二元性别者,但在现在的环境下,MtF无法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就会去选择女性身份。实际上如果社会足够多元包容,ta们足够勇敢,一些现在自称MtF的人可能会自我认同为非二元性别,或者是酷儿。”
曾经的阿云,会因为跨性别的身份而感到极大的焦虑,做手术的迫切需求、手术费来源的考量、家人和女友的认同,性别所带来的种种麻烦是她生活的核心。
现在的她却觉得,生活不只有性别这一个方面:“当你不把视角聚焦在自己的性别上时,可能会获得更多安心与平静。”
LGBTQ群体在自我觉察与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完成的不仅仅是对于身份的确认,还有对于性别本质与亲密关系更进一步的思考,这将会是一个长期且渐进的过程。抛开二元性别划分的桎梏,跳出异性恋亲密关系的窠臼,反而会使得一个人拥有更加自由地探讨爱与亲密关系的可能。
“我从没想过和一个人的关系可以这么深入。”尹青说,自己和挚友的关系很难简单用“朋友”一词概括。
她也曾和男生谈过恋爱——两个合拍的异性朋友,彼此之间有好感,性格合适、家庭背景相近,选择在一起,相处上有什么小问题,尝试沟通或者忍耐一下也就过去了,“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了搭把手过日子”。
对于过去的她而言,婚姻、家庭是人际关系想象的核心,丈夫则是陪伴度过人生的最重要之人。
现在的她在与挚友的关系里,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考。爱对方的原因不再是“适合”或“未来相近”,但只要是和未来相关的计划,对方就一定会被划入到自己的考虑范围里。
“我跟她之间的联结,不是出于经济考虑,不是因为社会规范,更不是因为他人告诉你一定要在合适的年龄组建家庭,而是因为爱。”
聊着两人的关系,回忆着高中生活的尹青,虽然语气听起来还是酷酷地漫不经心,脸上的笑容中却流露出略带羞涩的幸福和无比坚定的认真。
“这是我放眼整个经历中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遇见她,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假如说我要感谢我的性取向的话,这可能是我最为感谢它的一点——它让我有幸跳出异性恋的思维,去体验一段不一样的纯粹的关系。”
亲密关系的理想样态本应如此。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与社会规训,使得异性恋更容易或主动或被迫地进入某种关系的的桎梏之中。
而LGBTQ群体在尝试后,发现自己无法融入这一模式,于是他们跳出来,开始思考爱本身,最终发现:Love is love.
不再定义
对于LGBTQ群体而言,性别与性取向只是身份的一个面向,并不意味着全部的生活,不等同于决定性的刻板印象标签,更不等同于唯一的模式选择。
正如我们不会将异性恋视作一个具有高度共同点的单一群体,LGBTQ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多元的生活样态,人们有着属于自己的丰富生活,也有着自己的爱意与期待。
归根结底,“人”才是最根本的标尺,性别与性向,就如同信仰、口味偏好、喜欢的音乐风格一样,只是特征而已。如果你不会说“我们应当包容喜欢甜豆腐脑而不喜欢咸豆腐脑的人”,那你就不应当说“我们应当包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
“其实大多数人还是一种过日子的状态,而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一直处于抗争之中。”大能觉得,最终大家都在试图找寻着某种生活的平衡,尽管这本质上是某种无奈之举。
谈及未来想要做的事情,医学专业的小萨想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努力。过去的她想要探索生育技术的发展,但现在的她更想参与艾滋病治疗的相关研究。“如果能够不让LGBTQ群体与艾滋病传播者的标签挂钩,人们的接受程度可能会更高。”
2019年4月,微博女同性恋超话遭到封禁。在重建的尝试中,小萨曾经在微博写下这样一段话,直到今天,这一话语依然有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我们希望最终达成的,不是所谓的以我们的‘高尚’来标榜自身,也不是以我们的弱势而博得同情,得到广大异性恋施舍般的生存空间……从头到尾,我们只是在争取平等爱人和被人爱的权利。”
“不被恐惧”并不是最终的归宿,他们所想要的远不止于此,却又十分简单——不再被审视,不再成为想象的载体和附庸,不再被标签化,不再被消费,不再被窥探、好奇、体谅、包容,不再被观看,不再被强迫成为他人眼里的样子,而是成为自己。
感谢参与修改本文的阿云、大能、滴滴、飞鱼、小萨、尹青,也感谢接受访谈但并未在本文出现的其他朋友,最后要感谢转发或填写问卷的所有关注者,是大家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本篇文章。

2025.12.16 15:15
16
2025.12
16
2025.12
16
2025.12
 28:32
28:32
2025.06.19 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