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2022.06
1999年,跨过8200公里,彭凌从德国回到北京。那一年澳门回归,欧元诞生,北约轰炸南联盟,皇后乐队用一句“Empty spaces what are we living for”,直击时代岔口面前人群的矛盾与迷茫。
那也是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的开端。在孙家广院士的推动下,清华大学在国内率先展开软件人才的培养,成立计算机第二学士学位班,后来组建为应用技术学院,最终成为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的前身。
刚刚回国的彭凌成为应用技术学院三百多位学生背后唯一的教务老师。此后的十余年里,她从未离开学生工作的第一线。

2001年,彭凌(前排左二)与软件学院学生在北京世纪坛,参加申奥活动
图源:受访者
底色
2001年,清华大学软件学院正式成立,并于次年九月迎来第一批本科生。彭凌负责了院里全部的学生工作。
“从学生工作组组长,到兼任副书记,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学生工作助理,新生助理,就业助理,都是我一个人。”她说。
最早的办公室在昌平区200号,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院,距离校区车程40分钟。“那时候真是白手起家,条件是非常非常的艰苦。”她回忆道。教室没有窗帘,没有黑板,她就自己买。全院400多名学生,需要和家里通信,她就在学校买好邮票和信封,然后带回200号。所有人全部十门课的成绩,彭凌每个学期末都要在清华学堂独自录入。开学时则要添置电脑,要交学费,每个学生都带着满满的现金,彭凌用手比划着:“这辈子没数过那么多钱。”
但彭凌依然很喜欢那时候的200号,理由非常简单——“蓝天白云,还有水库。”

彭凌在200号
图源:受访者
彭凌的微信名是“喜欢大自然-THU”。朋友圈背景里,她戴着黑色圆礼帽,托着相机,包裹在彩色的长丝巾里。身后,是克拉玛依深浅不一的沟壑,裸露的石层被狂风雕琢得奇形怪状。
“我很喜欢旅行,走遍了五大洲,还有南极和北极。”聊起山水,彭凌显得格外亲切和热情。她的视频号里,有勐巴娜西珍奇园,漓江游船,靖边波浪谷,还有拉萨的一间长寿藏家宴。两个穿着藏服的小伙子在台上跳舞,她在背景里认真地解说:“这是一家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餐馆,是学生带我来的。”
疫情的到来打乱了生活原本的节奏。彭凌无比怀念2019年,这一年除了工作,她去了冰岛、格陵兰岛,去了北美,去了墨西哥,还去了朝鲜。今年年初各地疫情复发,她在朋友圈里回忆2020到2021年疫情好转的那阵子——“我去了广西去了张家界去了宁夏还有无数次重庆……”省略号的后面,她熟练地加上了三个 的emoji表情。
的emoji表情。
被疫情困住旅行步伐的彭凌在朋友圈仔细记录生活:家里阳台上的菜园长势喜人,香菜长得不错,折耳根能吃了,草莓在结果。食堂新上了网红麻花,她在桃李买了一个榴莲馅的,写道:“拿回家那个味 只有我一个吃。”
只有我一个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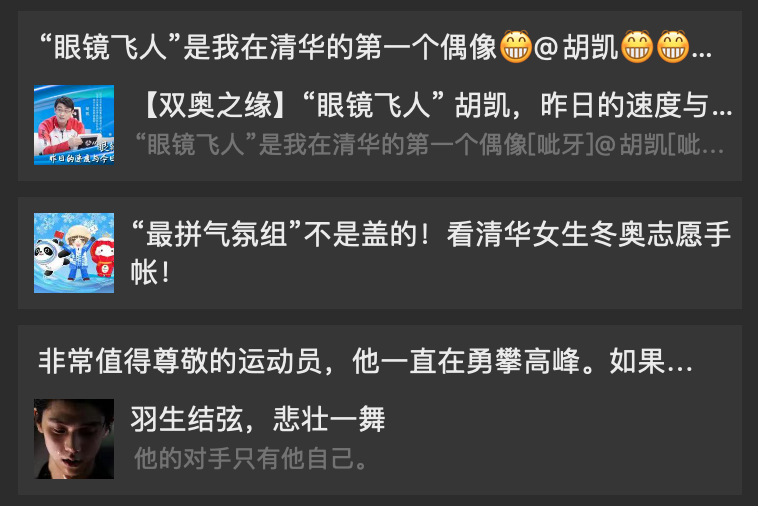
冬奥期间,彭凌分享的推送文章
图源:受访者
历史的刻印和岁月的无痕在年过花甲的彭凌身上得到一种奇妙的统一。她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的建设者之一,学院前党委副书记,履历上写满一整串学生工作荣誉头衔,参与和见证一门学科、一个学院从无到有的发展。在她的朋友圈里,每天都有轻快的生活分享,伴随满屏 和
和 的emoji。彭凌熟知朋克世代的种种流行元素,为了了解学生的喜好,她在车上让儿子放年轻人喜欢的歌。
的emoji。彭凌熟知朋克世代的种种流行元素,为了了解学生的喜好,她在车上让儿子放年轻人喜欢的歌。
彭凌仿佛从未与时代脱节,年轻人一样的洒脱始终是她生活的底色。
她还主持建立了二学位班的第一个学生BBS论坛——“出水芙蓉”,并成为“彭凌信箱”的版主。在那个电脑刚刚普及的年代,她通过邮件联系来默默了解每个学生,“信箱”也成为她抵达学生群体深处的载体。在这里,她和女孩们讨论面试妆容和服饰,和男孩聊世界杯。有些学生爱打游戏,彭凌就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不仅会打游戏,而且要打得比学生好”。
她记得在德国时玩过的一款赛车游戏,赢了就可以开进一个鸟语花香的“共产主义世界”,那里风景很美。
投入爱
有一年秋天,晚上十点多,彭凌接到一个新生的电话。电话那头,男孩站在东门外20层高的楼顶,晚风夹杂着怯懦的声音从听筒传来:“彭老师,您说过,我们的生命不仅属于我们自己,还属于父母,属于老师。所以我最后给您打个电话。”
男孩是失恋了,彭凌马上和同事一起把他接了回来。每每想起他,彭凌都有点后怕,但也很庆幸:“你看,学生信任你,把心里话提前告诉你,就不会出事。”
2013年退休后,彭凌成为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中心最繁忙的全职咨询师之一。学生都愿意和她聊爱情烦恼、学业焦虑,分享一些年轻人的私密心事。
彭凌听了太多故事。各异的成长背景、细腻复杂的心理感受,以及与成长有关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母题——“本科生焦虑的是学业和爱情,研究生焦虑的是爱情和学业。”

彭凌与学生交流
图源:受访者
她大抵是日渐多元和割裂的大学生活里,真正能够抵达学生内心的人。学生酒醉砸了别人的车,凌晨在派出所闹事,警察、舍友、女朋友的话都不听,一见到彭凌,马上变成“乖小孩”,嘴里嘀咕着,“彭老师,我没给清华丢脸”。冬夜,男生出校去女生宿舍楼下面求女朋友复合,“等不到就冻死”,最后也是彭凌出面帮两人和解。
“要是有一天我没钱吃饭了,我就专门写清华男生的爱情故事。”彭凌调侃道。
周围的老师始终好奇,学生为什么都愿意把故事讲给彭凌听?她的回答很直白:“学生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因为我爱学生,学生也爱我。”
十八岁时,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只在一瞬之间,而心智的成长却需要时间和阅历来积累。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远离家人,周围是陌生的朋友,此时的学生是孤独的。彭凌始终认为,学生在学校里可以犯任何错误,只要不违法。他的缺点和错误被老师发现指正了,他就不会再去社会犯更大的错。
“学生知道我骂他一顿是真心对他好,他们也能够认可。”她说,“他们有些在法律上是成年人,但心里还是小孩子。做学生工作就和做妈妈一样,只有你真心的爱他们,他们才会理解你、信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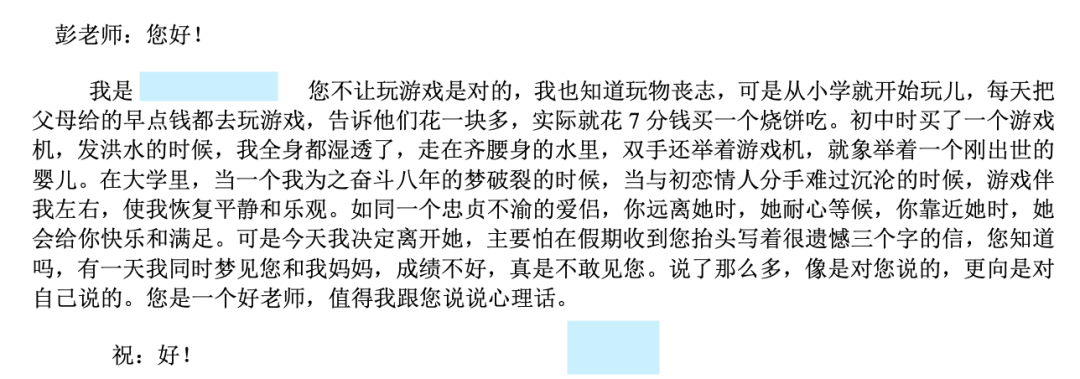
2001年,学生来信
图源:受访者
投入爱,被彭凌放在做学生工作的首位。这种爱不是对工作的热情,更多的是对学生本身的关注。它化解学生与老师间的疏离,把老师在大学教育中缺位的“育人”使命找寻回来,用真心的理解和平等交流来走进学生的内心。
“扶上马、送一程”,彭凌仔细衡量每一条路,试图为每一个求助的学生找到最适合的选项。
她记得曾经有一个博士生,在五年级的时候出了差错,意外没拿到毕业证书。他只能硬着头皮,拿着本科学历找工作。“整个人从原来很阳光的大男孩,一下子就萎靡了。简历拿给我一看,希望的工资:每个月4000块。”彭凌回忆道。她马上联系了已经毕业工作的学生,一番周折,为他找了份互联网大厂的实习工作,月薪一万块。

彭凌参与毕业典礼
图源:受访者
另一位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个立志选调的男孩。他的家庭环境已经很艰苦,老家的房子被大雨冲垮,一家人只能搬进邻居空闲的偏房寄住;后来父亲又出了车祸,瘫痪在床。
彭凌不是没有表达过反对意见:“选调生是赋能的,必须自己有余力,才能够去基层帮助更多的人。”但那个男孩却坚定地想要从政,打定主意走入基层。
后来的一次基层工作研讨会上,她看到这个学生的述职报告。他在当地已经结婚生子,工资不多,每个月的奶粉钱开销却不少,基层工作又要多送人情,生活得非常拮据。“吃不起肉,偶尔买条鱼。”他在报告中写。
“我自己也是经历过吃不起肉的年代。”彭凌说。她形容自己当时心情的变化,起初是难以置信,再一遍遍读他的文字,最后泪流满面。彭凌向学校相关部门和领导作了汇报,最终把他调回了老家,方便他照顾父母。
彭凌回忆起刚回国工作的时候,同事说的一番话,让她印象深刻:“每一个学生只是清华的两万分之一,而这两万分之一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又是每一个家庭的一半。”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学生,能够帮助就尽量帮助,也是在帮助一个家庭,她说。

专家聘书
图源:受访者
今年4月,彭凌发了一条九图朋友圈。粉红色的学生工作专家聘书,被八张校园风景照包围。聘书上是三行小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期盼您将育人理念、清华精神、科研清华通过「寻学热线」薪火相传,继续关怀青年教师发展,关爱青年学生成长。
“最大的快乐,就是看着学生们都过得好好的。”彭凌笑着说。
摆渡人
彭凌是很早“走出去”看一看的那群人之一。留学期间,她在欧洲生活,那时的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就是《秋菊打官司》里描绘的那样,“很落后的形象”。
“都这么多年了,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几乎没怎么变。”彭凌显得有些感慨。几年前的夏天,她的学生到加拿大访学,人们说你们中国是不是很落后啊,你看看我们的轻轨多好。学生就拿出家乡重庆的地铁照片给大家看,淡绿色的列车从李子坝的裙楼中穿行,开过鹅岭、佛图关、钟书阁、大渡口,最后抵达江畔。
早年的她辗转于两种文化之间,看过更广阔的天地。回国之后,这段早年经历指引着彭凌成为“摆渡人”,送家乡的孩子们走出大山,“出去看看”。
她每年参与家乡的招生工作,到重庆最偏远的中学去宣讲。曲折的盘山路要走几个小时,彭凌有时早上六点出发,辗转两所学校,夜晚才回到住所。

彭凌在重庆参与招生宣讲
图源:受访者
宣讲过的中学里,见过的孩子都叫她“彭妈妈”。彭凌也因此亲眼见证过许多命运的改变,更多时候,成为偏僻村庄里的第一个清华学生,意味着整个家庭命运的巨变。媒体的争相报道,政府出资修缮的老房子和茅厕所,还有父母的低保和弟妹的学费……一切都会因此得到着落。
彭凌经常用薛其坤院士的经历来鼓励孩子们。相比于那些从小浸润在琴棋书画里,以“状元之姿”来到大学的“天之骄子”,薛其坤研究生考了三次,博士七年才毕业,为了毕业练习了八十多遍英文演讲、硬把山东沂蒙山味儿的英语练到标准的故事,才是大山里的孩子们真正“可复制”的。
彭凌为每位考入软院的学生布置了一个“小任务”——用邮件写一封信。这封信是学生们迈向社会的“第一份文书”。每一封信的开头、落款,但凡有一处格式不符合要求,她都会要求学生仔细修改。
“当年很多刚入学的本科生同学连电脑开机关机都不会。”彭凌考虑了很多,“从这封邮件就能看出他是不是来自贫困家庭,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分门别类的提供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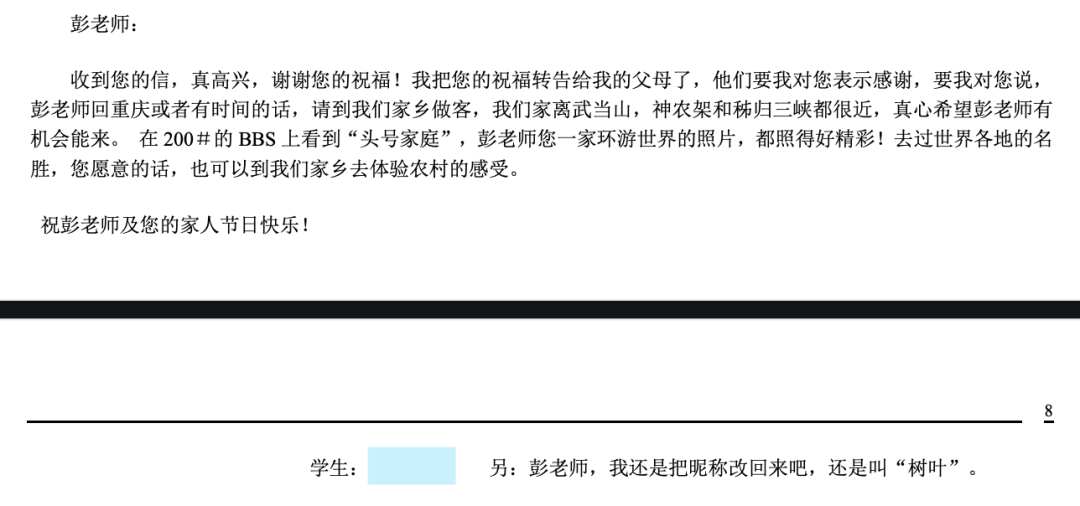
2001年中秋节,学生的邮件
图源:受访者
她是最能理解这群孩子的人。“我并不是一定要他们来清华。”彭凌说。更多的是要开阔眼界,化解掉山外的世界与孩子们的疏离感,让他们看到,除了挥之不去的困顿,未来生活的种种波澜可以闪耀到何种程度。
她也期待着,有一种人之为人的力量在山野里肆意生长——“就是希望,其实,我们的孩子在哪里都能发光。”
2022年5月,奥密克戎再次来到北京。彭凌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演唱会视频,台上的Avicii把话筒伸向观众,人群狂热的声音马上从背景里传来:
他说
总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世界
一定要活出值得自己铭记的人生
记住
这永不消逝的夜
她在下面附言:没有过不去的坎。

2023.08.14 13:45
05
2025.09
05
2025.09
09
2025.06
 28:32
28:32
2025.06.19 08:55